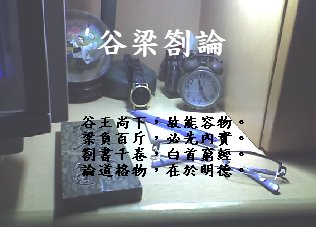(原RP1610老莊人生哲學take-home mid-term exam paper)
第一問:「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四十八章)一句常引起誤解,被理解為「表面上什麼都不做,暗地裡什麼都做」。你同意這種說法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無為」的概念?試討論你理解的方法或進路,並釐清以上誤解。
答:無疑,若以「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以解「無為而無不為」是悖於老子的的原意。若「無為而無不為」等於「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即假裝「不做」,那便是一種權謀巧智。然而,老子同時有言「智慧出,有大偽」(十八章)和「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六十五章)。因此可見,老子是反對以巧智治國。「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的讀法則不通。
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所以說,人最終應該效法「道」或者自然,老子有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三十七章),人的「無為而無不為」,實以效法「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然則,何謂道?老子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字之『道』」(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可見,「道」是創造、孕育萬物的主體。然而,「道」創造、孕育了萬物,令萬物自化自為,而不加明顯的干涉。日月、四時,都是「道」所推動的,「道」推動萬物的自化自為,而卻並非強加干涉於萬物,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由此亦可見,「道常無為」並非「道」常常甚麼都不做。只是「道」不強為,以致於「『道』隱無名」(四十一章)。人的終極目標是效法「道」和「自然」,「聖人」「無為而無不為」是效法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於是,「無為而無不為」則是不強為,但做很多事的意思。學者陳鼓應言:「『無為』一觀念,就是指順其自然而不加人為的意思。這裡所說的『人為』含有不必要的作為,甚至含有強作妄為的意思。」(《老子註譯及評介》)而學者劉笑敢就指出最有幫助理解「無為而無不為」的是「是故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第六十四章,竹簡甲本)(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第六十四章中「弗能為」作「不敢為」,亦疑為錯簡,然就解釋「無為而無不為」,劉說可取。)
返回《老子》原文,除了「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之外,提及「無為」有以下幾句: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章)
「為無為,則無不治」(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二十九章)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
「我無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六十三章)
當中,有兩次提及「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意指不用政令、規條式的督導,而潛移默化教化人民。如前所述,「道法自然」,即「道」純任自然,自己如是(陳鼓應的說法)。人最終的目標是效法道,「無為」是對應於「道」的「自然」。「聖人」透過「無為」最終希望民返回「樸」的狀態。
老子的想法,是相對於當時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逐漸失效,兵燹四起、國君、士大夫、平民各以巧智互相鬥爭,禮樂制度無法禁止。老子認為禮樂制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禮樂制度的形式化和人民相爭是不能避免。老子觀察到的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政令或施政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有反效果。他認為理想的統治者應該「無為」,其言:「我無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令萬物各歸其本位,各自然而生。「無為」是手段,「不言之教」是過程,「無不為」和「民自化」是結果。
正如劉笑敢在《老子古今》一書提出:「無為是聖人治理天下的方式,無不為是聖人輔萬物之自然的效果。」若將「無為而無不為」解作「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就會忽略《老子》一書的政治精神,又與前後相互矛盾。我並不同意將「無為而無不為」解作「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
第二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雲:「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司馬遷以「自隱無名為務」評老子之學,你同意這種說法嗎?你認為老子的哲學是「避世」「隱世」,還是「應世」「濟世」?試談談你的想法。
答:老子的思想是「應世」「濟世」而非司馬遷所指的「自隱無名為務」。《老子》一書有很強的政治色彩,透過《老子》一書可看出老子的政治思想,如「無為」、反對戰爭、反對形式化的禮樂制度,最後將社會風氣重歸於「樸」。在《老子‧七十章》有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正是他表明自己空有政治理想卻無人接納的悲傷。由此可見,老子並非消極避世、自隱無名為務,而是一個應世濟世的政治家。
首先,老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是「無為」,這是針對當時社會君主肆意妄為,民生困苦,盜賊益多下的藥。透過「無為」,希望社會能重歸於純樸,扭轉當時紛亂的局面,故此老子思想絕非避世。老子認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五十七章)、「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七十五章)。老子思前想後,將社會問題歸因於統治者的「有為」。統治者將其喜好強加於人民是又提倡巧智、貴賤是人民起紛爭的源頭。他指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章)。一個理想的統治者應該是「處無為之治,行不言之教」(二章),而令萬物各歸本位,各自然而生。想得出的效果正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由此可見,老子思想是應世的,老子亟欲改變當時的社會,不是避世隱世。
除此之外,老子強烈反對戰爭,他有濟世的胸懷,絕非獨善其身的犬儒。老子生於春秋時代,戰爭開始頻仍,諸候互相兼併,令生靈塗炭、餓莩遍野。老子傷感於時局,十分反戰,認為戰爭非到不得已都不會使用。例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 這是對於好戰的統治者作有力的控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三十一章)正正反映老子反戰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可見老子是「以百姓心為心」,他有強烈的濟世思想,非一般獨善其身不理世務的隱士能夠比較。
加之,他主張統治者節制個人的私欲。他指責統治者生活奢華,但人民十分困苦,他提倡「去泰」、「去奢」,希望改變社會。老子指出「朝其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兮。非道也哉!」(五十三章)老子斥責殘民以自肥的統治者是盜賊。又指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七十七章),控訴世道不公。然而,老子並不只懂控訴而沒有實際的政治主張。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十二章)、「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可以老子是並非犬儒,而是有實際的政治藍圖希望統治者遵從。
然而,司馬遷等卻將老子思想誤解成「自隱無名為務」,其原因有二。稷下道家思想、莊子的思想與老子的思想同被稱為「道家」。然而,稷下道家、莊子與老子有很明顯的不同。莊子追求「逍遙」的境界,思想較為出世。而稷下道家雜混了不同因素,而令老子的思想被扭曲。甚至有人指出《老子》是權謀之書,「無為而無不為」是「表面上甚麼都不做,暗地裡甚麼都做」。但是,老子思想是針對於當時社會的狀況,而非出世之士,故此老子思想並非避世、隱世的思想。
其次,就是對「無為」的誤解。老子的「無為」思想一般被誤解作「無所作為」或者「無立場」,既然不做或者無立場,就認為是出世、消極的思想。但其實這是把老子的「無為」思想誤解了。老子認為社會紛亂的原因是人們執於己見而與人爭論,所以人們應放棄「人為」的標準,遵循自然原則,不妄為,才能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老子的立場就是回歸自然,以「道」作為共同的立場,而非沒有立場。由此可知,「無為」並非避世思想。
總之,老子思想並非司馬遷所言「以自隱無名為務」,也不是避世、隱世的,反而是於當時對症下藥,亟欲希望將社會引導到人民生活安定、恬靜自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