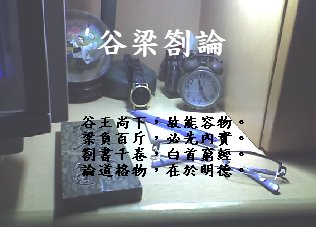一、前言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開始,這本來是邁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嘗試。在城市中,各級黨委動員在1958年年底總共動員了九千萬人進行「全民大煉鋼」,固然是乏善足陳,但煉鋼的失敗很快就被發生在農村的大饑荒搶奪了學者的眼光。從1958年開始,主要發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是人類史上罕見的發生在和平年代的大饑荒。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中國究竟餓死幾多人?」至今仍未有可信的官方數字,因此學者們都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試圖去估計當時有多人犧牲在這場「偉大」的躍進。本文試圖整理學者們的估算,嘗試找到一個較為靠譜的非正常死亡數字。另外,現在關於這個「三年困難時期」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本文不會嘗試去分析群眾心態或特定的個人是怎樣參與大躍進運動,但會試圖分析甚麼因素造成各地方非正常死亡比率有所差異。
二、大躍進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1982年中國進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後,於1984年同時公布1953年和1964年前兩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關於1953年和1964年的具體的人口數據主要是來自來。但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來自公安部的報告,公安部所依據的是戶口登記。由於死亡人數是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在當時報送中央和實際的數字均已不同,而即使是中央得到幾千萬的數字時,亦掩蓋而不公開,例如當死亡數字上呈到國務院時,周恩來下令銷毀,不得外傳。[1]而且,地方少報非正常死亡人數亦可以「吃空額」,在正常的情況下,多報人口意味生產隊被分配更多的生產任務,但在荒年時,多報人口意味可以獲得更多的「返銷糧」以賑荒。是故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亦即《中國統計年鑑‧1984》的數字,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是不可靠的。例如該年鑑載1959、1960、1961的總人口增加數分別為+1213萬、-1000萬和-348萬,三年的人口增加數總計為-135萬;但同時年鑑載3年的自然增長人數為+677萬、-304萬和+249萬人,三年總計自然增長人數為+622萬人。[2]當然,當年沒有發生過757萬人逃荒他國的事情,即使廣東陶鑄允許廣東省人民逃荒香港亦僅僅是很小規模,因此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很明顯是不可靠。
至今仍未有有確實數字的文件,因此,國內外的學者對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是基於估計。
1984年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根據1953、1964、1982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及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測算兩次人口普查間隔的歷年出笁人口和死亡人口,按線性趨勢求出1958至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700萬。[3]
蔣正華則以歷年的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然後找到58年至63年總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同時按這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因此,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299萬人減去6602萬人,等於1697萬人,約等於1700萬人。[4]蔣正華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數字是屬於較低的水平,但其58年至63年對死亡人數的數字與科爾的數字差異並不是很大。與之相比,科爾的數字是8626萬人,蔣的數字比科爾僅少了300萬人。[5]但主要引致蔣非正常死亡數字偏低的原因在於蔣的正常死亡人數數字偏高,因此當總死亡人數減去正常死亡人口,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數字就會偏低。
金輝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的研究所用的數字主要都是來自於《中國統計年鑑‧1984》和《中國人口年鑑‧1985》兩本官方數據。金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有1348萬人,[6]並假設1964年人口普查所調查的前幾年的出生率是基本可信的,因而推算1960和1961兩 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7]又取1956、1957、1962、1963四年的死亡率的平均值10.57千分比作「正常死亡率」,因而得出1960和1961年的正常死亡人數數字為1395萬再加上1959年的270萬,因而可以計算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不低於2791萬。金進一步指出市鎮人口在同期按公布的增長率仍增加了545萬人,而三年全國總人口則負增長135萬,算進去的話,則農村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達3471萬。
曹樹基的研究則是採用1953、1964和1982三次全國各縣市人口普查的數據,再參考各地地方誌中的記載,計算出各地災前、災後的人口增長速度,確定災前災後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人口減去1961年人口,所得淨減少人口,為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58-61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再加上淨遷移人口,就可以得出一地區之非正常死亡人口。然後合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245.8萬。[8]
而王維志對《中國統計年鑑‧1984》的數據有所懷疑。但他認為1959年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人數即+677萬人比人口增加數+1213萬更合符實際,因為在1958年已開始因大饑荒而令出生人數減少。因而得出1959年的人口數是66,671萬。再根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回推,得出1960和1961年的自然增長人口減少了2163萬。然後他假設公安部關於1959至1961年的人口出生數字基本可信,因此得出這三年的總死亡人數為5721.3萬。假設1958年的死亡人數781萬人為正常死亡人數,即可得出三年饑死的人數為3378.3萬。楊繼繩認為,1958年年底已出現餓死人的事件,781萬人中已有一部分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因此,楊將之修正為1956年至1958年三年的平均死亡人數作為正常死亡人數。[9]
筆者認為,王維志在前部關於人口數字的推算是正確的,但正如楊繼繩的質疑,1958年的死亡人口中有一部分已經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所以數字不準確,同時筆者亦不同意楊繼繩的使用某些年的死亡人口的平均數作為另某些年的正常死亡人口。不僅因為1958年的數字有問題而楊繼繩繼續使用已經有問題,而且,1959年至1961年人口亦有浮動。所以應按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總數,再按正常時期的死亡數字按人口比率作為1959年至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故宜從金輝的方法。按金輝用1956、1957、1962、1963的死亡率,即10.57千分比,再用王維志調整過的三年的人口數字,即:(66,671+65,171+64,508)*0.01057=2075.4萬,然後用王維志計算出的三年總死亡人口5721.3萬減去2075.4萬,所以,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字為3645.9萬。即1959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概是3646萬。這是筆者整理王維志和金輝的研究得出的數字。
三、大躍進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人民公社制度與1953年實施的「統購統銷」最大的分別是人民公社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是一級級的從上級得到派購的任務,在「浮誇風」越吹越大的時候,被省委和縣委指示的派購任務亦日增加重,因而形成農村農民口糧不足的情況。相反,在1958年1月實施戶籍制度之後,城市人口的基本口糧是以配給制獲取的。城市居民以「糧票」換取日用的食糧。因此是國家層面的計算和分配糧食予各省,各省分配給城市居民。因此對城市居民的影響較小。因而形成農村人口死亡比率較城市人口死亡比率較高的情況。據較為保守的《中國統計年鑑‧1984》的數字,1956和1957年的城市人口死亡率是7.43和8.47千分比,該三年的死亡率則為10.92、13.77和11.39千分比。相比農村的死亡率在1956和1957年是11.84和11.07千分比,在該三年卻一躍至14.61、28.58和14.58千分比。比較突出的是1960年,農村人口死亡率比起平時高出兩倍餘,相反城市人口死亡率比起往年,只是多了57%。
林毅夫和楊濤引用印度經濟學家森(Amartya Sen)關於食物獲取權的思路。在人均食物產出得到維持的情況下出現饑荒可能是因於部分人口稟賦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下降,也可能相對價格的劇烈變化,使部分人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10]林和楊用經濟計量的方法發現,在1959年至1961年嚴重供給衝擊下,一省的人均糧食產出和農村人口比例都是該省死亡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即人均糧食產出減少越大,死亡越多;城市人口佔該省的人口比例越高,該省的死亡率就越高。同時,衡量農業人口比例的變化對該省死亡率的影響大約比食物供應量彈性大72%。[11]換言之,這種傾斜城市的制度性因素比糧食減產是引起大饑荒的更為重要的因素。
而曹樹基將三年困難時期與與太平天國時期的比較的研究則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曹樹基將1959至1961年人口死亡率存在的省級差異和省內各府縣的差異與約一百年前(1850-1880)的太平天國之亂和回民起義所造成的人口減少一起分析。曹樹基的研究集中在十八省,他將一百年前和該三年的各省死亡比率排序,1的省份死亡率最高,18是最低。然後將100年前的排序與該三年的排序相加,發現除了安徽、甘肅、廣東和河北四地之外,其他十四省一百年之間人口的死亡程度達至平衡。[12]即一百年前太平天國和捻黨之亂對各省人口減少的影響和該三年的影響存在負關係。而在安徽和甘肅的分府的研究中,亦可以得出相關的結論。在這兩省的縣市,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後的死亡率同樣存在負關係。[13]
曹樹基認為林毅夫和楊濤的解釋不足之處在於,林和楊的解釋無法解釋為不同的農村地區受災的情況各自不同。而這正是曹的研究的問題點。曹曾假設19世紀下半葉的戰爭與饑荒造成若干地區的嚴重人口死亡,因此造成人地關係寬鬆,最終導致人均佔有土地資源和糧食資源的增加,在新的災難降臨之時,人均佔有土地資源較多的地區,更能化解災難。[14]惟曹在其關於各省糧食的研究推翻了自己的這個假設。於是,曹給予了新的解釋。他採用了「歷史記憶」一概念以作解釋。他指出經歷過大饑荒的地區對糧食的重視,遠遠超過未經歷過饑荒的地區,不論是民間百姓和基層幹部都如是。這種源於大饑荒的記憶,對糧食的高度重視,使這些地區很少出現糧食畝產量的大浮誇,即使虛誇亦幅度有限,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來自上級政府的高壓。[15]因而形成曹所描述的負關係。
筆者基本同意曹樹基的研究。但造成各省之間死亡率的差異不獨是一種遙遠的「歷史記憶」,而重為決定性的,是在1959年至1961年間各省長官的實質施政。曹樹基比較各省一百年之間的情況,例出四個省有例外的情況,包括有安徽、甘肅、廣東和河北。但正如曹樹基在其文中所述,安徽和甘肅是一百年前的主戰場,與1959年至1961年大饑荒沒有負關係,而另一些例如江蘇、浙江,則有負關係,證明相關的「歷史記憶」並非決定一省之內死亡率的最重要因素。
一個更為淺白易見的解釋是,各省所承擔的任務和各省領導的態度均有不同,因而對各省的災荒程度有所影響。負責指揮整個大躍進運動的是各省的省委,而中央部門並不實際參與大躍進運動的執行。與中央交流和在省內制定指標主要是各省省委的工作,因此各省省委書記便成為該省大躍進運動的最高負責人。所以,省委書記對大躍進運動的態度或是否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便成為決定各省災荒程度的重要因素。
以四川省為例,四川省在建國以後一直承擔著外調糧食的任務。而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合稱「四大左狂」。1952年,鄧小平調往中央工作,李井泉接任省委第一書記後,徵購糧從1953年的390萬噸增至1957年的498萬噸,而外調糧則由同期的53萬噸,增至290萬噸。相反,農業人口人均留糧只由233公斤微升至268公斤。[16]李井泉於1958年5月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亦是各省委第一書記僅有的一員政治局委員。東夫認為,對毛澤東而言,與其說是看重李井泉,不如說是看重他能拿出來的糧食。[17]因此,外調的糧食變成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政治資本。到1959年,李井泉依然要搞「萬斤田」,而且繼續堅持四川外調糧的政策,李說「全國都在依靠四川調糧。四川要突擊一下,把糧食運到交通沿線,便於調運全國。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如果完成不了就會影響全國。」李井泉曾經毛澤東保證,四川到1959年糧食產量可到6750萬噸,按30%的最低徵購標準,也比該年實際糧食產量1582噸要多。[18]在廬山會議後,李井泉亦曾以「保護幹部的積極性」為由,扣住在四川各地的國家倉庫的糧食,而不賑濟災民。[19]因此,四川省1959年徵購糧達到最高的601萬噸,但農業人口人均留糧僅139公斤,比1957年少了約100公斤。李井泉堅持其糧食外調任務而且不及時處理災情,因此形成四川省1958年至1962年940萬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佔全省人口的13.07%。[20]災後,在1964年普查時,人口數僅和1953年一樣。[21]
與四川有新明對比的是廣東。廣東人口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排第六,人口約是四川省的一半,而廣東1957年的農產量約是1007萬噸,而四川則是2131萬噸,[22]所以廣東的人均產量與四川沒有太大分別,亦算是農業大省。但廣東則沒有很多的外調任務。[23]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比較審慎,但在1958年7月,中南五省的農業協作會議上,廣東被指在追求「高指標」上,是明顯落後,陶鑄回廣東後就對省委的幹部說:「再不浮誇,就是態度的問題了。」[24]隨著廣東的躍進全面開展,陶鑄的頭腦也開始發燒,在秋天陶鑄號召農民「放開肚皮吃三頓干飯不要錢」。終到1958年年底出現糧食供給困難,1959年初,陶鑄又在廣東發動「反瞞產運動」,徵集在農村被農民藏起的餘糧以供城市之不足。到大概在四月,陶鑄的頭腦開始清醒,[25]因而在五月召開汕頭會議試圖控制虛報和徵購過多的情況,又在1960年困難時期撥出3.5億賑濟。[26]同時,亦不顧國家體面,允許農民逃荒香港,又允許香港接濟廣東省人。因此整個廣東在該三年的非正常死亡率僅佔1.71%。按曹樹基的排序廣東的非正常死亡率排在十八省的第十四。[27]
五、總結
以上分析了學者們對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字的估計,並列出三組原因解釋甚麼因素會影響一地區的非正常死亡率。由四川和廣東兩省比較可見,全國各地並不是鐵板一塊按城市與農村人口比例或「歷史記憶」決定非正常死亡率的高低,個別省份有沒有被指派任務和個別領導的態度顯然被(曹樹基)列入「其他因素」,但這個因素卻是最具重要性。
[2] 觀點由王維志提出,參見楊繼繩著,〈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資料可見於〈歷年人口自然變動情況1949-1980〉,載於《中國人口統計年鑑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頁355,384。http://www.yhcw.net/famine/Documents/popu005.html
[21] 1955年西康併入四川省,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西康和四川省是62,303,999+3,381,064 = 65685063人,1964年人口普查時四川省人口為67,956,490人,十一年間僅微增約2,000,000人,即大饑荒幾乎抵銷了近十年的出生人口。
[23] 廣東1957和1958年的糧食淨調出是10和45萬噸,四川則是299和192萬噸。見〈分省市歷年糧食凈調出量1957-1962〉,載於《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史料》(北京︰《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編輯委員會,1989),頁18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