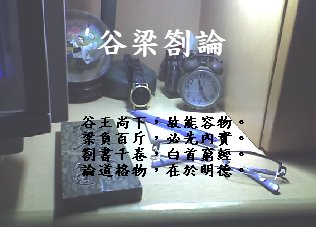(無錯!這次的還是term paper。這簡直就是儲存term paper 的地方!哈哈哈!不才樗櫟,或有斷章取義或曲解處。)
歷史是否中立?
歷史的定義若果僅僅是一堆堆發生過的事,那麼歷史並無所謂的立場,因為沒有人賦予它一些意義。但是若果歷史的定義不獨是這樣,而是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那就有所不同了。這樣,歷史就很難得到絕對中立了。
第一種原因是「偏見」(bias)。[1]是有先設立場、有價值觀的人接觸和篩選歷史,賦予它該時代的意義。因此,歷史變成有該時代觀點的獨有產物。這是由於「個人面對社會的活動並非一個冷眼的旁觀者,他參加社會生活,並看到自己是社會相互關係中的一員,所以他對社會生活的建設也有某種興趣,這種興趣本身又是五花八門的。它可能是一種純個人的利益,也可能是一種集團性的利益……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個人對社會問題和事件的看法與態度。」[2]
人的成長是經過「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社教化的主要功用就是社會再持續,而社教化最終會令到「人」(Man)在「社會」(Society)上被受約束,而「社會」亦都會植根在「人」的心中約束「人」。經過社教化以後,在「人」內在的「社會」就會成為一套價值觀、利益和道德。一個人的價值觀、利益和道德與另一人所以不同,是因為受了不同的社教化。因此,生長在中國的中國人與生長在美國的中國人是有所不同的。「思想」亦是一種價值觀,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被植入的價值觀亦不同。即使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也不能比時代走前很多步。
其中一例就是北宋(960-1127)名臣司馬光(1019-1086)。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主編。他的身份是士大夫,亦即是農業帝國的管治精英。他的時代背景是唐宋古文運動和理學的興盛,所以他的觀點會圍繞「王道」、「仁政」,範圍就是政治、軍事、經濟,人物就是君主、名臣。在他的作品之中,不會看不出甚麼富商傳奇、娼妓史、唐外來宗教如何傳入。
那麼為何今天有人為霍英東寫書?有些人或是受薪為富商寫書,或不,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對於商人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自法國大革命後,這些富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存在,他們是社會中有地位的人,並被冠以「名流」、「顯達」的名詞,我們受到的社教化形成我們這個概念。這是在傳統中國所不能想像,傳統中國的思想將社會分作四大階級「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所以「二十四史」中,很少為商人立「傳」,[3]立「傳」的大部分都是名臣或者名士。
所以不論是歷史學者的觀點或是取材,都無所謂絕對中立。
第二種就是「錯誤」(mistakes)。作者或歷史學家由於情感上的原因或利益原因刻意對某事某人有選擇性的或錯誤的描述,並非反映事件或人物事蹟的真象;或者是由於技術上的錯誤,並非刻意歪曲,令有些事件被錯誤理解。最終會影響整件事或人的客觀判斷。
前者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張列寧(1870-1924)演說的照片,在史太林(1879-1953)治下的蘇聯時代,在列寧演說台側邊的托洛斯基(Trotsky,1879-1940)被塗黑。另一著名例子就是1932年《紐約時報》刊登一張被炸彈燒傷的小童獨自坐在上海火車站的相片,有學者考證出底片中,小童後面是坐著大人。
技術性錯誤是十分容易理解,由於查證不太準確、錯誤抄錄或者作者自己記錯。在《霍英東全傳》一書亦屢見不鮮。就如書中158頁寫著:「1962年,他(霍英東)和湯於翰合資500萬港元,每人250萬,購入中環畢打街的畢打行。」但翻查舊報紙就會發現,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的《大公報》上寫著:「新業主為○商霍英東,成交價七百萬元。」由於《大公報》是一手資料,加上沒有利益衝突,可信性高,《大公報》說較可信。又,325頁提到北京飯店的貴賓房:「在亞運會期間,貴賓樓果然大派用場。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亞運會組委會租下了190套。」但一九九零北京亞運會期間,《大公報》於八月二十七日有這樣的報導:「貴賓樓位於現北京飯店西側……有高級客房、標準客房287間……」可見作者有誤引之嫌。
解決方法
歷史學有所謂「三C測試」(3 ”C” Test)。三「C」來自「可信性」(Credibility)、「內證」(Consistency)、「外證」(Corroboration)。「可信性」研究作者背景,寫書目的,以考慮書中內容是何等程度上可信。「內證」,比對書中是否有前後矛盾之處。「外證」,比對本書或他書對於同一件事和同一個人的描述是否有差異之處。結合三者,再尋找一手資料作為佐證。
通過這些方法能夠排除一些因情感上的原因或利益原因刻意對某事某人有選擇性的或錯誤的描述,或者是由於技術上的錯誤。因此較能反映一件事一個人的真象,並能較客觀地評價一個人和一件事,可以稱為「相對中立」。
然而,絕對中立仍是無法達到的。由「偏見」造成的不中立,並非歪曲事實或技術錯誤,所以不能用「三C測試」去修正。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偏見」,即使當代亦有「偏見」,例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等迷思。因此,所謂絕對中立仍是遙不可及。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想法
馬克斯‧韋伯是社會學家,他提出價值中立。他說:「調查者或教師應該無條件地分開實證建構出來的事實……和他的個人評價,不管他滿不滿意這個事實。」[4]意思是要中立的對待研究出來的結果,拋棄自身價值觀的影響。但韋伯亦不簡單地認為要把所有價值都要消去。價值亦存在意義。價值會幫助我們去選擇研究的題目。[5]套用到歷史學,價值的功用是為歷史學者或作者尋找重要的事去研究和闡釋。這也解釋到歷史學者知道了歷史並不是絕對中立,但研究歐美史的人數遠比中東史、非洲史的人數為多。
歷史哲學
黑格爾是(Hegel,1770-1831)是屬於德國唯心哲學流派的。他認為思想或意識改變,社會也會跟隨改變。他亦視這個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
他亦認為通過這些辯證的法則,就可以去到「絕對精神」的境界。姑勿論這個絕對精神是否能真的實現。黑格爾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思想或意識改變,社會也會跟隨改變;歷史行進的相續運動是為了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也意味著昨日的問題不是今日的問題,昨日的意識也不是今日的意識。隨着時間的變化,各个時代的人對同一件事的看法會發生根本變化,宋代不會把成吉思汗當作中國人。那麼昨日之種種意識已經不能為今日所用,大部分的歷史成為「封閉性因素」。[6]
那麼,就要回到一個問題:為何要讀歷史?一,研究這些「封閉性因素」。希羅多德在《歷史》的開首第一段寫著:「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在這裡呈上他的調查結果,旨在避免時間將人的勞績沖走,俾希臘人和外邦人的功業不致湮沒,也旨在解釋這兩族人何以發生衝突。」二,尋找「開放性因素」。[7]如文化史的研究。三,在「封閉性因素」中尋找意義。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1] 用「偏見」(bias)一詞作為第一類的名目,未必與其他學者所理解的一樣。不過這不是重點,這兒只是用以描述社教化影響下的偏見。
[2] [德]亨利希‧庫諾著,袁志英譯:《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頁555
[3] 例子如《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中的卜式是商人出身,他得入傳的原因是因為漢武帝北伐,他捐獻家財,成為佳話,及後亦為官。至於他如何發蹟,只有簡單兩句:「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數千頭,買田宅。」
[4] George Ritzer & D.J. Goodma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page 207
[5] 同上註。
[6] 指在過去適用,但現今不適用或不存在影響的因素。
[7] 相對於「封閉性因素」,指現今仍然能適用或存在影響的因素。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中國為何及如何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小序
哈哈哈!這次都也是term paper!不過這份比較特別,費時頗多。因為原本是2009/12/1日交,不才已經不可能殫思竭慮的做,但全文脈絡尚算清楚,加上要大量參考一手資料,是很好的嘗試!半年前與麟少討論過關於五四的事,涉及中國如何參與大戰,因此對此題目特別感興趣。大戰往往是被輕輕帶過的一章,寫完這篇文,大戰是民初的外國干預一個較好的範例。請請!)
引言
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其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的一個嘗試,而更直接的利益就是山東的權益。但一般史書對這段歷史卻著墨甚少,往往只提及由參戰問題而引起「黎段之爭」。一般的觀點亦不過認為段祺瑞借參戰為口實,向日本等國借貸,排抑地方勢力。紛紛指責軍閥統治的自私和賣國。然而,自1898年,德國強租膠州灣以來,大戰的爆發成為了收回山東權益的最好機會。
一,革命與爭取國際地位
對中國而言,辛亥革命意味著新時代的降臨。它結束了二千多年的中國帝制。封建君主制度的合法性存在被摧毀,這是一種新鮮的事。雖然中國在革命後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一如清廷,也無法得到解決。然而,革命思潮是澎湃的,它一氣地把舊中國帝制和新中國共和制割裂。以致即使袁世凱(1859-1916)於1915年或張勳(1853-1923)於1917年再次嘗試重建帝制,都是不得民心之舉,最終都趨向失敗。
辛亥革命無疑是中國自1860年代開始進行現代化的過程,在政治上一個最大的突破。亦是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性民族主義的來臨,這種民族主義是中國重建一種新的政治認同的手段。[1]而且,革命的民族主義亦帶有反帝國主義和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思想。加入國際社會,並最終在對外關係之中,實現其所處的國際地位的認同。
在兩次大戰未爆發之前,現代化等於西化成為了金科玉律。西方的就等於好的幾乎壟斷了思想。賀拔‧史賓莎(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發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正正印證這一點。若將達爾文從物種進化的觀點,強套入民族中間,東南亞的殖民化、中國被侵略可說純粹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結果。
因此,辛亥革命就更具意義了。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以來鼓吹的「共和精神」只有在少數國家如美國和法國得到落地生根,英國、德國、奧匈、俄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強權仍是君主立憲制或君主專制統治。辛亥革命是直接採用了西方思想最先進的政治制度。這對中國或者是外國是一樣震憾的。伍廷芳(1842-1922)說:「明日之中國將永遠不再是昨日之中國」,「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的公民;我們正在努力推翻這個反動的邪惡的專制的滿清政府,滿清政府不但使中國遭受貧窮和恥辱,而且還處處冒犯和對抗友邦,逆世界潮流而動」。 [2]而有西方人亦言:「中國使共和政體在世界範圍內的疆域擴大到世界總面積的三分一,並使共和國家總人口增加到原來的三倍,從而使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民都成為共和國家的一個成員」[3],同樣愛迪生(1847-1931)在評選1911年最重大政治事件,首選中國的辛亥革命。
中國走向世界亦具有更為現實的目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始不斷受外國欺凌,割地與租界問題、給予外國治外法權、關稅不自主、外國在中國駐軍、賠款都是列強透過戰爭強加於中國,中國成為國際的一員,就能提高其國際地位,能夠如日本和暹羅那樣,令外國自動放棄權益,諸如治外法權。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可謂是當中的良機。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互相廝殺,令中國的議價能力大增。中國的理想就是可一舉收回山東權益以及打進國際體系內。參與大戰,便成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國際化以致收回某些權益的一種嘗試。
二,大戰爆發時中國的反應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7月28日爆發,而到8月1日及3日,德國向俄國宣戰和法國宣戰,接著的就是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
消息傳到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或官員對此反響不小。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是給予中國的一次機遇,雖然當中亦有一點危機。但文化界和官員們對中國應該採取甚麼行動,卻莫衷一是。他們之中有親德派,有親協約國派,有中間派。
親德派最著名的有梁啟超(1873-1929)、陳獨秀(1879-1942)和徐樹錚(1880-1925)。梁啟超和陳獨秀都主張參戰,但他們的主場是親德的。這是由於德國強大的軍事力量給予不少中國人一個不能戰勝的形象,包括是徐樹錚。另外,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德國較之其他國家可說是較為溫和。梁啟超和陳獨秀都同意中國參與大戰是中國的莫大機遇。梁啟超指出,今日吾人承歐戰之潮流,而欲新國家之運命,仍以改造社會為第一要義。[4]而陳獨秀則認為中國參戰可「打破國亡種促之現狀」,走上「民主與科學」的道路。[5]他們的主張是透過參戰而得到內政和國際地位上的裨益。另一號代表人物只時陸軍次長徐樹錚,徐樹錚於1914年年底給山東德駐軍秘密送贈軍火,是為了中德兩國發展友好的關係。[6]
而親協約國派代表人物有梁士詒(1869-1933)、張國淦(1876-1959)、段祺瑞(1865-1936)。在大戰爆發之初,親協約國的主要是官員和軍人。梁士詒在和大總統袁世凱的一次徹夜長談就告訴袁,中國應抓住機會對德宣戰,中國只有對德宣戰才能收回青島,才能出席戰後和平會議,參戰合乎中國的利益。[7]由於此三人都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他們的意見對袁世凱有一定的影響力。
中間派的人數比較少,主要是革命志士,他們的聚焦不在向哪一邊靠攏,只在國內政治環境有利於討袁。[8]例如有孫中山(1866-1925)。孫中山其時留居在日本,他的看法都是認為大戰對中國是有利的良機,他說:「歐洲列強將無暇來考慮遠東的事務,賣國賊(袁世凱)也將因此不再借貸外債和購買外國的軍火」「這正是我們發動起義和武裝革命的時候。」[9]
無論是哪一派,都認為大戰對中國來說是莫大的機遇。然而,中國參戰的路途,並非如此一帆風順。
三,第一次嘗試參戰失敗
中國對於大戰爆發的反應不算緩慢。1914年8月6日,袁世凱下令恪守中立,並以1907年在海牙會議簽署的條約作為《局外中立條規》的延伸。[10]
與此同時,北洋政府向英國探聽日本的意圖。但英國保「不必擔心英日可能採取的任何聯合行動所帶來的後果」。8月1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親自聯系德國駐北京公使館詢問是否願意歸還膠濟鐵路。德國無暇東顧與日本人爭奪青島,因此願意有條件地交還山東主權。由於中國無錢贖回,加上得到英國的保證,再者是英國和日本的反對,英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朱爾典(J.N. Jordan,1852-1925)斷然告訴北洋政府,列強將不會承認中德的關於青島的協議。[11]因此,中國拒絕了德國的建議。
同時,袁世凱曾向英國提出過參戰要求。他向朱爾典提議提借五萬兵力與英攻克青島,但被朱爾典斷然拒絕。[12]
但另一邊的日本於9月3日便開始登陸山東攻擊德軍,並侵入了中國領土。因此梁士詒要求英國「確保日本在膠州問題上沒有歹意,而且要保護中國免受日本侵略」。[13]因此山東問題一直困擾中國,協約國不同意中國參戰拿回青島,又無法抵抗日本的野心。
四,《二十一條》的影響及第二次嘗試參戰失敗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Hiokil Eki)直接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總共有五號,分別關於山東特權問題、日本在外蒙和南滿的地位、關於漢冶萍公司、領土不讓與或租與他國,而第五號就關於中國主權。
無疑,日本是趁火打劫,以大戰打得如火如荼,協約國無暇與日本交涉,因此希望一舉獨吞中國的利益。日本為免列強干預,更要求中國嚴守保密,但北洋政府暗中洩露。莫理循在其書信中稱:「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國人嚴守秘密,接著僅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內容,從而國外造成一種騙人的虛假印象,結果是北京記者發電報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認為是『故意誇張』。」「英國外交部被告知日本政府提出十一條要求,而中國也一直同意討論這十一條。」[14]
然而,朱爾典是知道的,他說「我如果不指出歐戰的爆發以及日本的參戰嚴重損害了英國在華利益,那麼我作為英國的駐華公使將是失職的。」[15]事情經過廣泛的報導而激起民憤,3月18日,上海有四萬人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但最後,英國只是原地觀望。法國則同意了日本的《二十一條》的全部要求,明顯是出於無暇東顧,和希望得到日本支持。而中國最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只是於5月11日表示不承認,然而《二十一條》早於5月9日簽訂。
事實的結果是,日本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1915,5月9日,北洋政府和日本簽訂了一至四號,而沒有簽最侵害中國自主的第五號。
因此,這喚起中國參加戰後和平會議的動力。梁啟超便指出,日本確信其所要求的條件在戰後和會時決無通過之望,才匆匆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16]而法國駐華公使康悌(A.R. Conty)亦指出中國政府代表只有參加戰後和平會議,才能使中國問題可以不由各國隨意解決。夏詒霆還為中國可以加入戰後和平大會提出幾種方案。其一,聯絡美國,共同調停戰事。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第三條,當中立國調停交戰國衝突時,將來議和時可以自動出席和平會議。第二種方案是離間列強感情,以爭取中國的發言權。[17]
另一方面陸徵祥(1871-1949)於5月告訴袁世凱,只有參戰,中國才有望參加戰後和平會議。[18]於是參戰之事再被提起。由於梁士詒和張國淦等均是認為協約國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因此北洋政府需要再次拉攏英國和法國。1915年11月1日,蔡廷干致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19]的信寫道:「總統今日早晨說,他必須有一個,或者找到一個好的借口或者托辭,以便參加進去。請你為他找一個吧!」[20]莫理循同日回覆:「務請千萬小心,切不可在宣言裏露出它是為了防止日本侵略而發的任何痕跡。」[21]
中國的這種拉攏是透過捐款和供應槍械,亦允許英國和法國在中國招募華工上前線。1915年12月,朱爾典在信中談到「中國人對協約國的態度一直是相當友好的。他們以我所無法估量的方式給予了協約國實質性的援助,而且向各種戰爭基金會捐助了大筆金錢。」[22]除此,在11月底,梁士詒已制訂好一個詳細的援助英俄軍火計劃,並向兩國公使表示中國願意提供軍火。而且在9月,梁士詒便告訴康悌中國已經把三萬支步槍秘密送往英國。[23]
因此,在11月底,英俄法三國公使都勸中國加入協約國。1915年11月22日,駐英使館電外交部的文件中,寫著:「英俄法三使勸中國加入聯邦,已英文電告。關此電星期六已到,英政府先禁報載,今日始登。」[24]
此事引起日本的緊張。於11月22日,日置益「奉訓令來(外交)部詢問,中國政府提議願助英俄軍器,且可借款代造,並擬驅逐在華德人,與德為敵,是否屬實?」[25]1915年12月6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1866-1945)照會各協約國大使,正式反對所謂中國給協約國提供軍火援助的計劃。雖然協約國努力說服日本支持中國參戰,但最終失敗。
此時日本十分害怕「站錯隊」,因此日本反對協約國迫使她採取任何可能冒犯德國的行動。而新任的德國駐華公使發動猛烈的外交攻勢,試圖勸說日本脫離協約國。他表示德國不僅讓日本佔據青島以及太平洋諸島,而且將比協約國更加願意讓日本在中國自由行動。[26]
倘若日本與德國勾結,對協約國而言,形同一場惡夢。德軍在第二次伊普爾斯之戰無法突破英法軍,其後英法軍發動在羅斯反攻則傷亡慘重,西線仍在膠著,因此日本投敵對英法將是極大的打擊。英法俄三國都認為通過冒犯日本來爭取中國參戰是不明智的。為了確保日本站在協約國一邊,因此三國不僅拒絕中國直接參戰,而且還讓日本主導協約國的遠東政策。
因此中國第二次參戰計劃便胎死腹中。
五,1917參戰大辯論
直到1917年初,中國都沒有再提出參戰的要求。除了是中國缺乏那麼一個參戰的機會外,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內亂。1915年12月,袁世凱復辟稱帝,蔡鍔(1882-1916)逃到雲南,組成護國軍討袁,史稱護國戰爭。袁世凱於1916年3月退位,6月身故。其大總統遺缺由黎元洪(1864-1928)接任,段祺瑞則任國務院總理。整個1916年都平安無事。
但是,當美國於1917年2月3日向德國斷交,美國邀請中國一起行動,便成為中國向德宣戰的一個重要的前進。1917年2月9日,中國向德國提出了抗議。這個抗議明顯是借口,其一,中國並無船只往來,協約國有無封鎖與中國無關;再者,此次封鎖,英國先施,中國未有抗議於前。[27]
而更為有利的條件是日本不反對,甚至鼓動中國參戰。莫理循在1917年2月13日的書信寫道:「你無疑已經聽說對前天芳澤謙吉(1874-1965)[28]帶給總理(段祺瑞)的口信,和木野一郎子爵寫給東京中國公使[29]的信,中國人感到十分高興。木野一郎對中國採取的行動表示滿意,希望中國走得遠些,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係。」[30]
導致日本態度轉變的原因是山東權益已牢牢的掌握在手中。英日兩國早在年初便達成協議。1917年2月14日,英國正式通知日本:
「英國政府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欣然同意作出以下保證,即英國在和平會議上就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以及赤道以北諸島的歸屬問題上將支持日本的要求;同理,日本政府也將……本著同樣精神對赤道以南的德國所屬島嶼歸屬問題上支持英國的主張。」[31]
同時,日本可以利用段祺瑞內閣的參戰計劃而擾亂中國的內政,進而加強其干預,更何況美國已經給予中國邀請,日本難以反對。
然而,抗議德國之事及其後的參戰計劃在中國輿論引起另一種迴響。參考學者徐國琦的分類,可分四大派。四大派之中的人物是互相交疊,或者同時身跨幾派。
依徐說,第一派是維持現狀派。該派包括一些工商團體以及一些官員,他們認為強權勝於公理,中國是弱國,抗議是毫無意義,德國既無傷害到中國的利益,不必庸人自擾。而中國與德國斷交更有可能招惹戰爭。其代表人物有湖南督軍譚延闓(1880-1930),[32]以及一些國會議員如唐寶鍔。[33]
第二類為親德派,代表人物有康有為(1858-1927)。該派人士認為中國想振興和富強,德國就是中國的榜樣。即使德國戰敗了,仍然有能向中國報復。加上,列強劃定勢力範圍時,中國得以保存是因為列強在亞洲的利益均衡。康認為中國積弱,無力對德開戰,應該專注內政建設。他認為中國應放棄參戰帶來「千載一時之機,一躍以為頭等之國,空言誇耀,中風狂走」的迷思。[34]
第三派為防日派。該派認為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總是伺機侵奪更多的利益。中國參戰只是會令日本趁機通過各種借貸或其他方式對中國造成更大的危機。中國參戰只會有利於日本,因此中國應該堅拒參戰。代表人物有官員李經羲(1859-1925),他更認為日本與之前相反,轉而支持中國與德國斷交,實在是居心叵測,建議慎重行事。[35]
第四派為政治反對派。代表人物有孫中山。孫中仙所反對的並不是參戰,而是段祺瑞政府。他認為弱國跟隨大國參戰,輸家總是弱國。如果中國要宣戰應該向俄英法宣戰,而不是對德宣戰。他還設法勸其他列強不要支持中國參戰。可見其態度相當飄忽。1917年6月8日,孫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1856-1924),說「一幫賣國賊,以保全中國利益為借口而宣戰,但他們的真實意圖是恢復君主專制……實際上是為了獲得一己之利……」[36]
但是,反對的思想始終屬於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支持中國加入協約國。於是國會在1917年3月11日表決中國參戰時,參議院158票贊成,37票反對。眾議院331票贊成,84票反對。於是3月14日,大總統黎元洪發表對德絕交布告
八,黎段之爭與正式參戰
1917年3月11日國會已大比數通過與德絕交。但在此之前,有一段風波。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偕同全體閣員到總統府,要求大總統黎元洪在致日本政府電報上簽字。段內閣希望探知日本對中國參戰目標的反應。這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段認為日本的反對已經令中國兩次參與戰爭受挫。
但黎元洪則認為事關重大,需要先經由國會通過。他認為這樣的建議實際上是為宣戰做準備,黎認為應先徵求有宣戰權的國會通過。段憤而提出辭職,離京赴天津。後在馮國璋(1859-1919)調解下,段返京,並經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
但去到4月25日,在中國準備討論對德宣戰案之前,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省長召開「督軍國會議」,7位督軍、2位督統、1位省長、16位代表中,多數支持參戰。[37]那些督軍團成員在北京期間,要求列席閣議,甚至拜訪駐京公使,企圖干預外交事務。段個性剛毅,1915年袁稱帝時,就因不滿袁所為而引退。在對德宣戰之事上,段自大戰爆發來,每天閱讀關於大戰的材料。[38]並暗地裏為參戰做準備。[39]現在,段得督軍團支持,就可以藉以向總統和國會施壓,以求其宣戰案能夠通過。然而,為甚麼國會原本已以大比數通過對德斷交,為何段還要多此一舉?一般書籍較少提及。
其一,對戰爭如何進行有所分歧。其中有一派認為中國不應加入協約國,而應與美國一致行動。例如馮國璋於4月30日一封書信中就認為「與其加入協約國,或反為條約所束縛,不如徑與美一致進行,猶能操縱在我。」[40]
其次,翻查莫理循的書信,可以發現他在5月9日的書信中寫著:
「2月9日,中國向美國和德國分別提出一份照會。幾天以後,她向協約國的公使們打聽,他們是否贊成把關稅提高到值百抽五……2月14日,寺內正毅(1852-1919)[41]派了一個名叫西園龜三(1872-1954)的秘使來到北京。西園龜三使中國人相信,日本答應給予中國比她自己提出更為優厚的條件。日本還答應運用她對盟國的影響取得她們同意。受了這些諾言的欺騙,段祺瑞於3月8日向國會宣佈,一旦中國參戰,各大國就同意提高關稅,延期十年償付義和團賠款,並撤出各國駐扎在北京和鐵路線上的衛隊。
這位總理3月8日在國會所作協約國駐華使節業己答應中國所提條件的聲明,是協約國駐華使節們從未知道……段祺瑞這時發覺因為日本賴掉西園龜三許下的諾言,自己已在無意中陷入欺騙國會的地位。日本非但反對把關稅提高到值百抽五以上,甚至連值百抽五也是處在強大壓力下的日本政府所不肯答應的。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國會已被欺騙,國會對此憤慨異常。」[42]
於早前的4月11日,莫氏亦在信中提及:
「他(西園龜三)讓中國人相信,日本政府準備支持中國在3月14日向協約國提出的那些要求,並由段祺瑞向國會作出由於這些要求的不恰當以致引起誤解的聲明……」[43]
可見,在關稅問題上,段祺瑞是因為上了日本的當,使段在國會信用大失,故才透過督軍團的壓力冀望盡快令國會通過投入戰爭。但其實,參戰案原本可以順利通過,民初政治史學生陶菊隱指出,國會大部分的議員原本已贊成段對德宣戰。[44]但段及其部下錯估形勢,試圖讓參戰案強行通過。
5月8日,宣戰案開始在眾議院討論。督軍團為了確保國會通過宣戰案,不惜動用暴力。5月10日,幾千名自稱「公民請願團」的人群聚集在眾議院門前,圍困議員,不肯撤離,除非通過宣戰案。他們又威脅燒毀國會,謀殺議員。十餘名議員被毆打或騷擾。
5月11日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1861-1918)四位閣員,抗議國會議員被辱,提出辭職。5月15日國務院再咨眾議院對德宣戰案。5月19日眾議院以多位內閣閣員辭職,而催議咨文乃用國務院名義於法律不合,議決緩議對德宣戰案,須先進行內閣改組。段揚言要解散國會。5月23日,黎免去段的總理職務,段宣稱由此造成的任何後果,他概不承擔。
之後,在段祺瑞的策動下,安徽、奉天等八省先後宣布「獨立」。黎元洪請督軍團團長張勳入京調解。張勳對黎元洪提出條件,必須「解散國會」。黎被迫答應,並於6月13日發布命令解散國會。6月14日張勳入京後,擁立溥儀復辟。
後段祺瑞逐走張勳,重返北京。黎元洪萬分羞愧,引咎辭職。由馮國璋接任總統。段祺瑞由於與舊國會於5月間因宣戰案發生衝突,因此他反對恢復舊國會,段祺瑞稱事件為「再造共和」,指舊國會已被解散,原有法統亦已不再存在,於是與梁啟超等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孫中山與他的追隨者便在南方諸省表示反對,另組新政府。從而形成南北對峙。
自與德斷交以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終於1917年8月14日,正式對德奧宣戰。
總結
無論在大戰爆發初期的哪一邊都認同這是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和得到國際認同的一個良好機會。袁世凱無能擺脫國際環境的掣肘,始終無法能夠從大戰中獲取甚麼利益。
到段祺瑞為總理,結束了袁世凱行的是「寡頭政治」。雖然黎元洪只是被供奉的神主牌,但段祺瑞仍在形式上相當尊重這個大總統和國會。只是宣戰案卻一舉摧毀了這種表面的和諧。
正如徐國琦所言:「在國內政治危機出現之前,段祺瑞參戰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然而少年共和國參戰之際,又衍生出一個更加緊迫的問題。現在,段祺瑞的首要問題是要統一中國。要成為中國的大一統者,段祺瑞需要借助參戰問題來加強他的權力以統治的合法性。」[45]
不僅如此,宣戰案導致的不幸事件更破壞了中國脆弱的共和,最終令軍閥時代和南北對峙的降臨。
中國參戰,由開始的時候已經是為了爭取國際認同和收回山東權益。但到了,1919年,山東權益仍然不到手,更令人沮喪的是,參戰成為一個「塞拉耶佛事件」,從此,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黑暗時期,直到1927。中國為了大戰有著重大的付出,提供軍火、金錢、華工,既得不到山東權益,國際地位亦不見得怎樣提高,反而是日本的侵略逐步迫近。正正應驗了一句說話:「弱國無外交」。
參考資料:
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3.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
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一)》及《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
5. 汪朝光:《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國的初建(1912-192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6. 【美】徐中約著,計秋楓、鄭會欣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7. 【英】李德‧哈特著,林光餘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出版,2000)
[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57
[2]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9
[3] 同上註,頁41
[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87。
[5] 同上註,頁89。
[6] 同上註,頁90。
[7] 同上註,頁93。
[8] 1913年,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引致「二次革命」,後被袁世凱令鎮壓,最後孫中山和黃興東逃日本,北洋政府和原同盟會的革命份子關係破裂。
[9] 參見上註,頁88。
[10]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383。
[1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92。
[12] 同上,頁94。
[13] 同上,頁95。
[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頁403-404。
[15] 同註十一,頁97。
[16]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00。
[17] 同上註,頁101。
[18] 同上註,頁103。
[19] 莫理循於其時為《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亦是袁世凱的政治顧問。
[20]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頁498。
[21] 同上註,頁499。
[22] 同註十六,頁106。
[23] 同上註,頁109。
[2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頁392
[25] 同上註。
[26]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11-112
[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頁1149
[28] 芳澤謙吉時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參贊。
[29] 日本中國公使,時為曹汝霖(1877-1966)
[30]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20
[3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88
[32] 參見〈譚延闓關於德領對我抗陳述六點意見致段祺瑞抄電〉,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49
[33] 參見〈唐寶鍔等對德抗議質問書〉,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52-1160
[3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11。
[35]參見〈李經羲為對德關係致段祺瑞函〉,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49-1151。
[36] 同註三十五,頁221。
[37] 汪朝光:《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國的初建(1912-192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170。
[38]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91。
[39] 同上註,頁93。
[4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頁1190。
[41] 寺內正毅時為日本首相。
[42]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42。
[43]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31。
[4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27。
[45]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21。
哈哈哈!這次都也是term paper!不過這份比較特別,費時頗多。因為原本是2009/12/1日交,不才已經不可能殫思竭慮的做,但全文脈絡尚算清楚,加上要大量參考一手資料,是很好的嘗試!半年前與麟少討論過關於五四的事,涉及中國如何參與大戰,因此對此題目特別感興趣。大戰往往是被輕輕帶過的一章,寫完這篇文,大戰是民初的外國干預一個較好的範例。請請!)
引言
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其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的一個嘗試,而更直接的利益就是山東的權益。但一般史書對這段歷史卻著墨甚少,往往只提及由參戰問題而引起「黎段之爭」。一般的觀點亦不過認為段祺瑞借參戰為口實,向日本等國借貸,排抑地方勢力。紛紛指責軍閥統治的自私和賣國。然而,自1898年,德國強租膠州灣以來,大戰的爆發成為了收回山東權益的最好機會。
一,革命與爭取國際地位
對中國而言,辛亥革命意味著新時代的降臨。它結束了二千多年的中國帝制。封建君主制度的合法性存在被摧毀,這是一種新鮮的事。雖然中國在革命後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一如清廷,也無法得到解決。然而,革命思潮是澎湃的,它一氣地把舊中國帝制和新中國共和制割裂。以致即使袁世凱(1859-1916)於1915年或張勳(1853-1923)於1917年再次嘗試重建帝制,都是不得民心之舉,最終都趨向失敗。
辛亥革命無疑是中國自1860年代開始進行現代化的過程,在政治上一個最大的突破。亦是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性民族主義的來臨,這種民族主義是中國重建一種新的政治認同的手段。[1]而且,革命的民族主義亦帶有反帝國主義和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思想。加入國際社會,並最終在對外關係之中,實現其所處的國際地位的認同。
在兩次大戰未爆發之前,現代化等於西化成為了金科玉律。西方的就等於好的幾乎壟斷了思想。賀拔‧史賓莎(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發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正正印證這一點。若將達爾文從物種進化的觀點,強套入民族中間,東南亞的殖民化、中國被侵略可說純粹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結果。
因此,辛亥革命就更具意義了。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以來鼓吹的「共和精神」只有在少數國家如美國和法國得到落地生根,英國、德國、奧匈、俄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強權仍是君主立憲制或君主專制統治。辛亥革命是直接採用了西方思想最先進的政治制度。這對中國或者是外國是一樣震憾的。伍廷芳(1842-1922)說:「明日之中國將永遠不再是昨日之中國」,「我們正在努力成為世界的公民;我們正在努力推翻這個反動的邪惡的專制的滿清政府,滿清政府不但使中國遭受貧窮和恥辱,而且還處處冒犯和對抗友邦,逆世界潮流而動」。 [2]而有西方人亦言:「中國使共和政體在世界範圍內的疆域擴大到世界總面積的三分一,並使共和國家總人口增加到原來的三倍,從而使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民都成為共和國家的一個成員」[3],同樣愛迪生(1847-1931)在評選1911年最重大政治事件,首選中國的辛亥革命。
中國走向世界亦具有更為現實的目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始不斷受外國欺凌,割地與租界問題、給予外國治外法權、關稅不自主、外國在中國駐軍、賠款都是列強透過戰爭強加於中國,中國成為國際的一員,就能提高其國際地位,能夠如日本和暹羅那樣,令外國自動放棄權益,諸如治外法權。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可謂是當中的良機。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互相廝殺,令中國的議價能力大增。中國的理想就是可一舉收回山東權益以及打進國際體系內。參與大戰,便成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國際化以致收回某些權益的一種嘗試。
二,大戰爆發時中國的反應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7月28日爆發,而到8月1日及3日,德國向俄國宣戰和法國宣戰,接著的就是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
消息傳到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或官員對此反響不小。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是給予中國的一次機遇,雖然當中亦有一點危機。但文化界和官員們對中國應該採取甚麼行動,卻莫衷一是。他們之中有親德派,有親協約國派,有中間派。
親德派最著名的有梁啟超(1873-1929)、陳獨秀(1879-1942)和徐樹錚(1880-1925)。梁啟超和陳獨秀都主張參戰,但他們的主場是親德的。這是由於德國強大的軍事力量給予不少中國人一個不能戰勝的形象,包括是徐樹錚。另外,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德國較之其他國家可說是較為溫和。梁啟超和陳獨秀都同意中國參與大戰是中國的莫大機遇。梁啟超指出,今日吾人承歐戰之潮流,而欲新國家之運命,仍以改造社會為第一要義。[4]而陳獨秀則認為中國參戰可「打破國亡種促之現狀」,走上「民主與科學」的道路。[5]他們的主張是透過參戰而得到內政和國際地位上的裨益。另一號代表人物只時陸軍次長徐樹錚,徐樹錚於1914年年底給山東德駐軍秘密送贈軍火,是為了中德兩國發展友好的關係。[6]
而親協約國派代表人物有梁士詒(1869-1933)、張國淦(1876-1959)、段祺瑞(1865-1936)。在大戰爆發之初,親協約國的主要是官員和軍人。梁士詒在和大總統袁世凱的一次徹夜長談就告訴袁,中國應抓住機會對德宣戰,中國只有對德宣戰才能收回青島,才能出席戰後和平會議,參戰合乎中國的利益。[7]由於此三人都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他們的意見對袁世凱有一定的影響力。
中間派的人數比較少,主要是革命志士,他們的聚焦不在向哪一邊靠攏,只在國內政治環境有利於討袁。[8]例如有孫中山(1866-1925)。孫中山其時留居在日本,他的看法都是認為大戰對中國是有利的良機,他說:「歐洲列強將無暇來考慮遠東的事務,賣國賊(袁世凱)也將因此不再借貸外債和購買外國的軍火」「這正是我們發動起義和武裝革命的時候。」[9]
無論是哪一派,都認為大戰對中國來說是莫大的機遇。然而,中國參戰的路途,並非如此一帆風順。
三,第一次嘗試參戰失敗
中國對於大戰爆發的反應不算緩慢。1914年8月6日,袁世凱下令恪守中立,並以1907年在海牙會議簽署的條約作為《局外中立條規》的延伸。[10]
與此同時,北洋政府向英國探聽日本的意圖。但英國保「不必擔心英日可能採取的任何聯合行動所帶來的後果」。8月1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親自聯系德國駐北京公使館詢問是否願意歸還膠濟鐵路。德國無暇東顧與日本人爭奪青島,因此願意有條件地交還山東主權。由於中國無錢贖回,加上得到英國的保證,再者是英國和日本的反對,英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朱爾典(J.N. Jordan,1852-1925)斷然告訴北洋政府,列強將不會承認中德的關於青島的協議。[11]因此,中國拒絕了德國的建議。
同時,袁世凱曾向英國提出過參戰要求。他向朱爾典提議提借五萬兵力與英攻克青島,但被朱爾典斷然拒絕。[12]
但另一邊的日本於9月3日便開始登陸山東攻擊德軍,並侵入了中國領土。因此梁士詒要求英國「確保日本在膠州問題上沒有歹意,而且要保護中國免受日本侵略」。[13]因此山東問題一直困擾中國,協約國不同意中國參戰拿回青島,又無法抵抗日本的野心。
四,《二十一條》的影響及第二次嘗試參戰失敗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Hiokil Eki)直接向大總統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總共有五號,分別關於山東特權問題、日本在外蒙和南滿的地位、關於漢冶萍公司、領土不讓與或租與他國,而第五號就關於中國主權。
無疑,日本是趁火打劫,以大戰打得如火如荼,協約國無暇與日本交涉,因此希望一舉獨吞中國的利益。日本為免列強干預,更要求中國嚴守保密,但北洋政府暗中洩露。莫理循在其書信中稱:「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國人嚴守秘密,接著僅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內容,從而國外造成一種騙人的虛假印象,結果是北京記者發電報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認為是『故意誇張』。」「英國外交部被告知日本政府提出十一條要求,而中國也一直同意討論這十一條。」[14]
然而,朱爾典是知道的,他說「我如果不指出歐戰的爆發以及日本的參戰嚴重損害了英國在華利益,那麼我作為英國的駐華公使將是失職的。」[15]事情經過廣泛的報導而激起民憤,3月18日,上海有四萬人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但最後,英國只是原地觀望。法國則同意了日本的《二十一條》的全部要求,明顯是出於無暇東顧,和希望得到日本支持。而中國最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只是於5月11日表示不承認,然而《二十一條》早於5月9日簽訂。
事實的結果是,日本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1915,5月9日,北洋政府和日本簽訂了一至四號,而沒有簽最侵害中國自主的第五號。
因此,這喚起中國參加戰後和平會議的動力。梁啟超便指出,日本確信其所要求的條件在戰後和會時決無通過之望,才匆匆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16]而法國駐華公使康悌(A.R. Conty)亦指出中國政府代表只有參加戰後和平會議,才能使中國問題可以不由各國隨意解決。夏詒霆還為中國可以加入戰後和平大會提出幾種方案。其一,聯絡美國,共同調停戰事。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第三條,當中立國調停交戰國衝突時,將來議和時可以自動出席和平會議。第二種方案是離間列強感情,以爭取中國的發言權。[17]
另一方面陸徵祥(1871-1949)於5月告訴袁世凱,只有參戰,中國才有望參加戰後和平會議。[18]於是參戰之事再被提起。由於梁士詒和張國淦等均是認為協約國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因此北洋政府需要再次拉攏英國和法國。1915年11月1日,蔡廷干致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19]的信寫道:「總統今日早晨說,他必須有一個,或者找到一個好的借口或者托辭,以便參加進去。請你為他找一個吧!」[20]莫理循同日回覆:「務請千萬小心,切不可在宣言裏露出它是為了防止日本侵略而發的任何痕跡。」[21]
中國的這種拉攏是透過捐款和供應槍械,亦允許英國和法國在中國招募華工上前線。1915年12月,朱爾典在信中談到「中國人對協約國的態度一直是相當友好的。他們以我所無法估量的方式給予了協約國實質性的援助,而且向各種戰爭基金會捐助了大筆金錢。」[22]除此,在11月底,梁士詒已制訂好一個詳細的援助英俄軍火計劃,並向兩國公使表示中國願意提供軍火。而且在9月,梁士詒便告訴康悌中國已經把三萬支步槍秘密送往英國。[23]
因此,在11月底,英俄法三國公使都勸中國加入協約國。1915年11月22日,駐英使館電外交部的文件中,寫著:「英俄法三使勸中國加入聯邦,已英文電告。關此電星期六已到,英政府先禁報載,今日始登。」[24]
此事引起日本的緊張。於11月22日,日置益「奉訓令來(外交)部詢問,中國政府提議願助英俄軍器,且可借款代造,並擬驅逐在華德人,與德為敵,是否屬實?」[25]1915年12月6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1866-1945)照會各協約國大使,正式反對所謂中國給協約國提供軍火援助的計劃。雖然協約國努力說服日本支持中國參戰,但最終失敗。
此時日本十分害怕「站錯隊」,因此日本反對協約國迫使她採取任何可能冒犯德國的行動。而新任的德國駐華公使發動猛烈的外交攻勢,試圖勸說日本脫離協約國。他表示德國不僅讓日本佔據青島以及太平洋諸島,而且將比協約國更加願意讓日本在中國自由行動。[26]
倘若日本與德國勾結,對協約國而言,形同一場惡夢。德軍在第二次伊普爾斯之戰無法突破英法軍,其後英法軍發動在羅斯反攻則傷亡慘重,西線仍在膠著,因此日本投敵對英法將是極大的打擊。英法俄三國都認為通過冒犯日本來爭取中國參戰是不明智的。為了確保日本站在協約國一邊,因此三國不僅拒絕中國直接參戰,而且還讓日本主導協約國的遠東政策。
因此中國第二次參戰計劃便胎死腹中。
五,1917參戰大辯論
直到1917年初,中國都沒有再提出參戰的要求。除了是中國缺乏那麼一個參戰的機會外,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內亂。1915年12月,袁世凱復辟稱帝,蔡鍔(1882-1916)逃到雲南,組成護國軍討袁,史稱護國戰爭。袁世凱於1916年3月退位,6月身故。其大總統遺缺由黎元洪(1864-1928)接任,段祺瑞則任國務院總理。整個1916年都平安無事。
但是,當美國於1917年2月3日向德國斷交,美國邀請中國一起行動,便成為中國向德宣戰的一個重要的前進。1917年2月9日,中國向德國提出了抗議。這個抗議明顯是借口,其一,中國並無船只往來,協約國有無封鎖與中國無關;再者,此次封鎖,英國先施,中國未有抗議於前。[27]
而更為有利的條件是日本不反對,甚至鼓動中國參戰。莫理循在1917年2月13日的書信寫道:「你無疑已經聽說對前天芳澤謙吉(1874-1965)[28]帶給總理(段祺瑞)的口信,和木野一郎子爵寫給東京中國公使[29]的信,中國人感到十分高興。木野一郎對中國採取的行動表示滿意,希望中國走得遠些,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係。」[30]
導致日本態度轉變的原因是山東權益已牢牢的掌握在手中。英日兩國早在年初便達成協議。1917年2月14日,英國正式通知日本:
「英國政府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欣然同意作出以下保證,即英國在和平會議上就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以及赤道以北諸島的歸屬問題上將支持日本的要求;同理,日本政府也將……本著同樣精神對赤道以南的德國所屬島嶼歸屬問題上支持英國的主張。」[31]
同時,日本可以利用段祺瑞內閣的參戰計劃而擾亂中國的內政,進而加強其干預,更何況美國已經給予中國邀請,日本難以反對。
然而,抗議德國之事及其後的參戰計劃在中國輿論引起另一種迴響。參考學者徐國琦的分類,可分四大派。四大派之中的人物是互相交疊,或者同時身跨幾派。
依徐說,第一派是維持現狀派。該派包括一些工商團體以及一些官員,他們認為強權勝於公理,中國是弱國,抗議是毫無意義,德國既無傷害到中國的利益,不必庸人自擾。而中國與德國斷交更有可能招惹戰爭。其代表人物有湖南督軍譚延闓(1880-1930),[32]以及一些國會議員如唐寶鍔。[33]
第二類為親德派,代表人物有康有為(1858-1927)。該派人士認為中國想振興和富強,德國就是中國的榜樣。即使德國戰敗了,仍然有能向中國報復。加上,列強劃定勢力範圍時,中國得以保存是因為列強在亞洲的利益均衡。康認為中國積弱,無力對德開戰,應該專注內政建設。他認為中國應放棄參戰帶來「千載一時之機,一躍以為頭等之國,空言誇耀,中風狂走」的迷思。[34]
第三派為防日派。該派認為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總是伺機侵奪更多的利益。中國參戰只是會令日本趁機通過各種借貸或其他方式對中國造成更大的危機。中國參戰只會有利於日本,因此中國應該堅拒參戰。代表人物有官員李經羲(1859-1925),他更認為日本與之前相反,轉而支持中國與德國斷交,實在是居心叵測,建議慎重行事。[35]
第四派為政治反對派。代表人物有孫中山。孫中仙所反對的並不是參戰,而是段祺瑞政府。他認為弱國跟隨大國參戰,輸家總是弱國。如果中國要宣戰應該向俄英法宣戰,而不是對德宣戰。他還設法勸其他列強不要支持中國參戰。可見其態度相當飄忽。1917年6月8日,孫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1856-1924),說「一幫賣國賊,以保全中國利益為借口而宣戰,但他們的真實意圖是恢復君主專制……實際上是為了獲得一己之利……」[36]
但是,反對的思想始終屬於少數。大多數的人都支持中國加入協約國。於是國會在1917年3月11日表決中國參戰時,參議院158票贊成,37票反對。眾議院331票贊成,84票反對。於是3月14日,大總統黎元洪發表對德絕交布告
八,黎段之爭與正式參戰
1917年3月11日國會已大比數通過與德絕交。但在此之前,有一段風波。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偕同全體閣員到總統府,要求大總統黎元洪在致日本政府電報上簽字。段內閣希望探知日本對中國參戰目標的反應。這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段認為日本的反對已經令中國兩次參與戰爭受挫。
但黎元洪則認為事關重大,需要先經由國會通過。他認為這樣的建議實際上是為宣戰做準備,黎認為應先徵求有宣戰權的國會通過。段憤而提出辭職,離京赴天津。後在馮國璋(1859-1919)調解下,段返京,並經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
但去到4月25日,在中國準備討論對德宣戰案之前,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省長召開「督軍國會議」,7位督軍、2位督統、1位省長、16位代表中,多數支持參戰。[37]那些督軍團成員在北京期間,要求列席閣議,甚至拜訪駐京公使,企圖干預外交事務。段個性剛毅,1915年袁稱帝時,就因不滿袁所為而引退。在對德宣戰之事上,段自大戰爆發來,每天閱讀關於大戰的材料。[38]並暗地裏為參戰做準備。[39]現在,段得督軍團支持,就可以藉以向總統和國會施壓,以求其宣戰案能夠通過。然而,為甚麼國會原本已以大比數通過對德斷交,為何段還要多此一舉?一般書籍較少提及。
其一,對戰爭如何進行有所分歧。其中有一派認為中國不應加入協約國,而應與美國一致行動。例如馮國璋於4月30日一封書信中就認為「與其加入協約國,或反為條約所束縛,不如徑與美一致進行,猶能操縱在我。」[40]
其次,翻查莫理循的書信,可以發現他在5月9日的書信中寫著:
「2月9日,中國向美國和德國分別提出一份照會。幾天以後,她向協約國的公使們打聽,他們是否贊成把關稅提高到值百抽五……2月14日,寺內正毅(1852-1919)[41]派了一個名叫西園龜三(1872-1954)的秘使來到北京。西園龜三使中國人相信,日本答應給予中國比她自己提出更為優厚的條件。日本還答應運用她對盟國的影響取得她們同意。受了這些諾言的欺騙,段祺瑞於3月8日向國會宣佈,一旦中國參戰,各大國就同意提高關稅,延期十年償付義和團賠款,並撤出各國駐扎在北京和鐵路線上的衛隊。
這位總理3月8日在國會所作協約國駐華使節業己答應中國所提條件的聲明,是協約國駐華使節們從未知道……段祺瑞這時發覺因為日本賴掉西園龜三許下的諾言,自己已在無意中陷入欺騙國會的地位。日本非但反對把關稅提高到值百抽五以上,甚至連值百抽五也是處在強大壓力下的日本政府所不肯答應的。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國會已被欺騙,國會對此憤慨異常。」[42]
於早前的4月11日,莫氏亦在信中提及:
「他(西園龜三)讓中國人相信,日本政府準備支持中國在3月14日向協約國提出的那些要求,並由段祺瑞向國會作出由於這些要求的不恰當以致引起誤解的聲明……」[43]
可見,在關稅問題上,段祺瑞是因為上了日本的當,使段在國會信用大失,故才透過督軍團的壓力冀望盡快令國會通過投入戰爭。但其實,參戰案原本可以順利通過,民初政治史學生陶菊隱指出,國會大部分的議員原本已贊成段對德宣戰。[44]但段及其部下錯估形勢,試圖讓參戰案強行通過。
5月8日,宣戰案開始在眾議院討論。督軍團為了確保國會通過宣戰案,不惜動用暴力。5月10日,幾千名自稱「公民請願團」的人群聚集在眾議院門前,圍困議員,不肯撤離,除非通過宣戰案。他們又威脅燒毀國會,謀殺議員。十餘名議員被毆打或騷擾。
5月11日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1861-1918)四位閣員,抗議國會議員被辱,提出辭職。5月15日國務院再咨眾議院對德宣戰案。5月19日眾議院以多位內閣閣員辭職,而催議咨文乃用國務院名義於法律不合,議決緩議對德宣戰案,須先進行內閣改組。段揚言要解散國會。5月23日,黎免去段的總理職務,段宣稱由此造成的任何後果,他概不承擔。
之後,在段祺瑞的策動下,安徽、奉天等八省先後宣布「獨立」。黎元洪請督軍團團長張勳入京調解。張勳對黎元洪提出條件,必須「解散國會」。黎被迫答應,並於6月13日發布命令解散國會。6月14日張勳入京後,擁立溥儀復辟。
後段祺瑞逐走張勳,重返北京。黎元洪萬分羞愧,引咎辭職。由馮國璋接任總統。段祺瑞由於與舊國會於5月間因宣戰案發生衝突,因此他反對恢復舊國會,段祺瑞稱事件為「再造共和」,指舊國會已被解散,原有法統亦已不再存在,於是與梁啟超等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孫中山與他的追隨者便在南方諸省表示反對,另組新政府。從而形成南北對峙。
自與德斷交以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終於1917年8月14日,正式對德奧宣戰。
總結
無論在大戰爆發初期的哪一邊都認同這是中國提升國際地位和得到國際認同的一個良好機會。袁世凱無能擺脫國際環境的掣肘,始終無法能夠從大戰中獲取甚麼利益。
到段祺瑞為總理,結束了袁世凱行的是「寡頭政治」。雖然黎元洪只是被供奉的神主牌,但段祺瑞仍在形式上相當尊重這個大總統和國會。只是宣戰案卻一舉摧毀了這種表面的和諧。
正如徐國琦所言:「在國內政治危機出現之前,段祺瑞參戰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然而少年共和國參戰之際,又衍生出一個更加緊迫的問題。現在,段祺瑞的首要問題是要統一中國。要成為中國的大一統者,段祺瑞需要借助參戰問題來加強他的權力以統治的合法性。」[45]
不僅如此,宣戰案導致的不幸事件更破壞了中國脆弱的共和,最終令軍閥時代和南北對峙的降臨。
中國參戰,由開始的時候已經是為了爭取國際認同和收回山東權益。但到了,1919年,山東權益仍然不到手,更令人沮喪的是,參戰成為一個「塞拉耶佛事件」,從此,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黑暗時期,直到1927。中國為了大戰有著重大的付出,提供軍火、金錢、華工,既得不到山東權益,國際地位亦不見得怎樣提高,反而是日本的侵略逐步迫近。正正應驗了一句說話:「弱國無外交」。
參考資料:
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3.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
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一)》及《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
5. 汪朝光:《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國的初建(1912-192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6. 【美】徐中約著,計秋楓、鄭會欣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7. 【英】李德‧哈特著,林光餘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出版,2000)
[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57
[2]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9
[3] 同上註,頁41
[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87。
[5] 同上註,頁89。
[6] 同上註,頁90。
[7] 同上註,頁93。
[8] 1913年,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引致「二次革命」,後被袁世凱令鎮壓,最後孫中山和黃興東逃日本,北洋政府和原同盟會的革命份子關係破裂。
[9] 參見上註,頁88。
[10]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383。
[1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92。
[12] 同上,頁94。
[13] 同上,頁95。
[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頁403-404。
[15] 同註十一,頁97。
[16]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00。
[17] 同上註,頁101。
[18] 同上註,頁103。
[19] 莫理循於其時為《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亦是袁世凱的政治顧問。
[20]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頁498。
[21] 同上註,頁499。
[22] 同註十六,頁106。
[23] 同上註,頁109。
[2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外交》,頁392
[25] 同上註。
[26]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11-112
[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頁1149
[28] 芳澤謙吉時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參贊。
[29] 日本中國公使,時為曹汝霖(1877-1966)
[30]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20
[31]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188
[32] 參見〈譚延闓關於德領對我抗陳述六點意見致段祺瑞抄電〉,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49
[33] 參見〈唐寶鍔等對德抗議質問書〉,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52-1160
[3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11。
[35]參見〈李經羲為對德關係致段祺瑞函〉,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頁1149-1151。
[36] 同註三十五,頁221。
[37] 汪朝光:《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國的初建(1912-192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170。
[38]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91。
[39] 同上註,頁93。
[4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政治(二)》(南京:江蘇古藉出版社,1991),頁1190。
[41] 寺內正毅時為日本首相。
[42]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42。
[43]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631。
[44]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27。
[45] 【美】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頁221。
訂閱:
意見 (Atom)